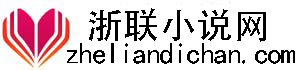60-70(30/37)
想去中兴府了。数日后,他看到了贺兰山。
他们没有更多的告别,没有依依不舍的挥泪,只有沉默的马蹄声,顺着两条岔路蔓延开去。
他褪下身上的衣服,将买来的劣质伤药涂到了手臂的伤口上,曾经无暇的皮肤,如今已经叠着许多的伤。
饥饿与虚弱让他几乎站不起来,可光渡还是要出去觅食。
他们仓促地奔向离别。
光渡在山中找到了一个勉强避风的洞穴。
宋沛泽语气很平静,但一字一句,都让车中的人听得清楚,“听我的,一会你们两个先走,骑马走。别担心我,我一个人反而更容易脱身。”
马车转动的车轮,缓缓变慢,及至停下。
光渡已经没有太多力气了,但求生的渴望,支撑着他最后这一口气,他顺着血迹追了不知道多久,整个人都摇摇晃晃。
宋沛泽跳下马车,把马从车上解下来,这是他刚刚从宋人营地抢来的,就是预备着这一刻。
可对面已经发现了他。
从此以后,抛却姓名,抛弃过往。
人太多了,光渡被逼上了贺兰山。
……
熬了几夜的眼睛通红着,可是他的头脑,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冷下来过。
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愈发虚弱,可惜几次进城买的药,都没什么作用,或许是不对症,药效远远不如自己的朋友几针扎下去那般,来得立竿见影。
这空旷荒芜的雪山上,仿佛只有他一个人,山腰上只有呼啸的寒风,再也没有别的声音。
临出发前,光渡禄同紧紧抓着宋沛泽的胳膊,“我们走了,你怎么办?今天早上我们经过那个城镇时,你已经被西北边的城镇通缉了,现在到处都在找你,到处都说你杀了好多人。”
面前出现了第一个岔路时,光渡勒住了马。
出城后,少年在乡野间找了个废弃无人的破房过夜。
“留你下来,还能有命活下来吗?”宋沛泽对他说话的语气,从来没有那刻像现在这般温柔,“……你有此劫,本就是受我兄妹连累,我已负你良多,不能再害你。”
她年纪小,难道不知道沛泽一个人去应付,会有多危险吗?
光渡禄同红着的双眼,不可置信的转而望向了宋雨霖。
没有人来。
宋雨霖本能道:“哥哥,我不要跟你分开!”
但他终于找到了那只被他弓箭射中的岩羊,那只羊倒在地上时,身上还带着他的箭。
尽管他自己都不确定,能不能在那里见到自己的亲人和朋友。
本来,他是想在这漏风的房中对付过一个夜晚,可合眼不过半个时辰,他又警觉地睁开了眼。
同时将卸掉马的马车,推下了山崖,山间树木受力折断,留下深深的车辙压痕。
只是上面画的人像,并不像他。
前路漫漫,而这世间,从此再无宋沛泽。
妹妹真的要抛下沛泽吗?
他是光渡,他必须习惯这个名字。
少年扒着门缝看了片刻,没走正门,从另一边的窗子跳出离开。
驻兵在名册上登记,不耐烦挥挥手,“下一个。”
光渡扒开岩羊的血管,直接生饮羊血,羊尸体还是温的,这是光渡几天以来的第一口有温度的食物。
孤山天地,雪风萧瑟,光渡稍稍缓了过来,才烧火吃肉,狼吞虎咽之后,所有的疲惫都漫了上来。
他正在未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