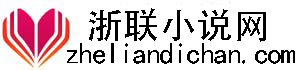第15章 黄金手(1/7)
在与雪雨湾共哺一河的弗林锡城,夜色笼罩,整座城市沉浸在片死寂之中,凛冽的风呼啸着穿梭在狭窄的街巷,发出如鬼哭狼嚎般的声响,仿佛是褶皱山将所有寒冷都倾泻而下,吞噬殆尽一切温暖与生机,以报复这个城市对它掏心挖肺般的采矿攫财。
寒风中,两辆陈旧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在街道上行进,木质车轮咯吱吱碾压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,让车前两盏防风灯随着马车的颠簸晃荡,昏黄的灯光在寒风中摇曳闪烁,好似随时都会熄灭,为马车增添了几分老态龙钟般的迟钝,就像两个在黑暗中蹒跚而行的垂暮老人。
渐渐的,马车缓缓来到宽阔幽暗的长街尽头,停在了座竖着石柱遮风灯的宅子前,这宅子被笼罩在片朦胧的夜色里,四周的围墙爬满了枯萎的藤蔓,在风中瑟瑟发抖,宛如张张张扭曲的鬼脸,而那斑驳的松木门紧闭,透着股静谧又神秘的气息。
两名身披黑色斗篷的年轻人轻轻叩响了大门,在听到有人时忙小声道:“告诉你家主人,神的使者到了。”说着紧紧握着斗篷下的剑柄,似乎在防备着什么。
不一会儿,大门缓缓打开,火光从门缝中透出,随即一名老者举着火把,探出半个身子,眯着眼睛打量了半天,慢吞吞道:“里面请!”说完,不紧不慢打开大门,开始在前面带路。
门外马车上陆续下来十几名年轻护卫,他们簇拥着名头戴斗篷、露着蓬松灰白胡子的魁梧男人,迈入院中,并小心翼翼打量着四周,而院落的墙壁上,偶尔有几株不知名的植物在寒风中挣扎着,叶片呈现出诡异的紫色,在火把的映照下,投下片片怪异的影子。
众人在看门老者的领路下,穿过很多巷道小门,每经过一扇门,都能听到门轴转动时发出的的刺耳声音,好似是在提醒这座宅子主人客人所在的位置,终于,在七拐八拐后,一座护民官会客厅般的大理石房子出现在人们面前,敞开的房子正正方方,三面光滑如镜的墙壁中央摆着帐厚实的桌子,屋子两脚放置着两盏高大的雕刻立灯,暖黄色的灯光洒在地面上,与外面的黑暗形成鲜明的对比,里面一个穿着灰布长袍、花白短发的中年男人坐在张宽大的木桌前,正用竹管笔在银墨盒中蘸着墨汁,他的眼神专注而深邃,似乎在考虑好什么重要事宜后,笔尖在洁白的羊皮纸上划过,快速书写着什么,并时不时回头向身边一个二十多岁的卷发书记员低声问话,两人的交谈声如此之低,好似周围的桌椅都会窃听窥秘。
门外来客的侍从们摘下遮脸的帽子,他们的脸上带着疲惫和警惕,依旧紧抓斗篷下的银头长剑柄,压着声音道:“吾王驾到,众人避让。”然而,屋里的人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,花白短发男人仍旧低头卷起封羊皮信,将印鉴戒指在油灯上烤了烤,蘸着火漆将信件封好,又随手将桌子上两个锡碗拨拉到边上,开始写另一封,旁边的年轻书记员抬头看了眼屋外的人们,随即低头整理手边的十几封羊皮信。
风吹过,引路老者的松油火把冒出阵阵黑烟,将屋外灰白胡子男人呛得不停咳嗽,男人只好摘下斗篷帽,露出张饱经沧桑又红润油亮的脸,抬头望着屋内,等待良久后,终于忍耐不住地声音低沉道:“尊敬的润士?丹爵士,我亲爱的兄弟,你难道不欢迎我吗?”声音中似乎带着些许不满。
这时,屋里的男人润士?丹终于抬起头,眨眨眼,好似有些惊讶般道:“查瑞?”随即向门外勾勾手,又开始埋头用竹管笔写信。
查理尼二世尴尬地站在原地,片刻后,又自嘲地撇撇嘴,迈步走进屋子,满脸堆笑地站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