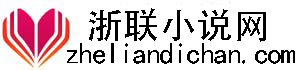40-50(25/34)
他只能珍重地把人勾勒一圈又一圈。“怎么了你,去广州一趟被毒哑了,话都不会说了,盗墓案件进展怎么样。”余晏丈二摸不到脑袋。
脸还是那张脸啊,英俊到找不到瑕疵,怎么突然傻了。
席澍艰难说:“还好……我事情办完就先回来了,海关拦截的确实是秦东陵的陪葬品,追回了一百多件,送到省文物局了。”
“嗯,你怎么穿得这么厚,发烧了吗?”余晏走进两步,抚了下他额头。
挺正常的啊,难不成是人不正常了。
余晏狐疑地目光探究过去:“你不对劲,你今天太不对劲了,席队。”
席澍避开他的眼神:“哪里不对劲了,我这两天体寒,在外面冷到受不了所以穿了件外套。”
“哪个外面。”余晏一下就抓到了他话头的漏洞。
“出…”席澍还保留最后一丝理智,广州这时候还热着呢,“出机场的时候。”
“那你有点体虚啊,我给你预定个中医看看吧,八十岁老头都还没套羽绒服的天气,你先套上了。”余晏幽幽道。
这人指定是瞒了他些什么,而且还不是小事。
真可爱。
席澍脑子里跳出来三个大字,他转移话题:“家里有没有东西吃,我肚子饿了。”
“没有。”余晏很果断。
席澍脑中如同麻线团一样,太过凌乱了,不知如何回应:“那我定些宵夜吧,你想吃什么。”
“都可以。”余晏见他没有聊下去的意思,便也不自找没趣,自顾自钻进了自己的房间。他已经订了去昌凤市的飞机票,今天晚上得理好行李。
他身影消失在视线中,席澍才沉沉地吐出口气。
作足了心理准备,才一步踏着一步往房间中去,每一步好似踏在他心尖上,把碾压在他身上的巨山推倒。
房间泛黄的主灯下,在衣帽间忙前忙后的余晏显得格外安详,也就是表面罢了。他这个从小被宠大的少爷,十指不沾阳春水,哪里会整理衣服。
把收纳师归置的衣柜,折腾得乱七八糟。从小上学的时候,连包都不肯自己背,睡前他还得帮他检查笔墨课本有没有带整齐。
席澍蓦然觉得双腿发沉,整个人直直要往下坠,肺腑内袭来的绞痛让他连身子都站不直了。
“你收拾行李是要去那儿。”
余晏被惊了下,从搅成一团的衣服里头钻出来:“我去趟东北昌凤市。”
“为什么要去东北。”席澍是个混不吝的,此刻却踌躇不前,似是而非地问着。
余晏默了下,慎重回答:“我想去找一个人。”
“是谁。”
他仓惶错开席澍固定在他身上的视线:“是我的一个朋友,他死了,我想去看看他的遗体。”
翻涌奔腾的热意简直让席澍肺腑都化成软流,灼伤他每寸骨肉。
他问:“阿晏,你是怎么死的。”
余晏猛然回头,喉头滚动了下,如同被胶水粘住声带,他半晌说不出话。
“余晏,1902年生于西京,1933年去世,生不见人死不见尸。告诉我,当年发生了什么。”席澍居高临下,迸发出一种不容违逆的气势。
余晏失神地站了起来,所有思绪仿佛被他的目光所掠夺走,连呼吸中都带了涩气,无力地张了两下嘴。
席澍叫他……余晏?
他本以为这辈子都无法从他口中听出这两个字了,他本以为一辈子都要套在成聿安这个壳子里苟且偷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