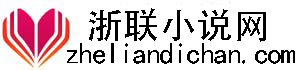50-60(19/34)
以今夜,他不能进涵元殿。这就是他徘徊的缘故。
云蓝说:“世子若不喜欢,推辞了便是。”
崔琰松了手,冷冷望着眼前女子。她似乎对他睡哪个女人,都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
她难道忘了他交付她的重托了?
他反问她:“朕可以推辞。但你既然知道,告诉朕就是你的分内之事,你为何瞒朕?莫非对你而言,此事,你乐见其成?”
云蓝被他的重话说得又出了冷汗,仰着眸子,指尖轻攥。
她思索着,他一定在想,他的确可以推辞,只是会伤了他姨母萧夫人的面子,所以,若她开口邀他去她的承明殿过一夜,自然再好不过,全了各自的脸面,让这事解决得不必太难看。
他一定也在想,她今日却没有一点儿平日里替他排忧解难的觉悟。
可……可她若是不知此事,他去承明殿,她再高兴不过了;偏偏叫她知道了,在她还不知他心中到底怎么想之前,她怎么能坏了他的“好事”。
若他心中的确对那位谢小姐有意呢?
若是那样,她落了个争风吃醋的不是。
她咬着唇瓣,压下喉咙间的咳嗽,大抵是风吹久了,又耗了不少心神。缓着呼吸,好半晌,她才轻声说:“上回世子教诲,臣妾铭记于心,不会再犯,所以臣妾才没有言明。”
她心头原本遇他在此的欢喜,此时也尽皆褪去,行了礼,准备自己回承明殿了。
子夜时分,朔风浩雪,宫道上格外寒冷,她吹风吹了很久,有些头晕眼花。
想来他现下生气,责怪她不明事理,也不会再陪她回宫,不如不抱这个期望的好。
他却又阴沉沉地叫她:“朕没准你回去。”
云蓝心头一跳,酒意醒了泰半,忽然担心,不会这回他要叫她在这儿罚站了吧?这可糟糕。
她停在原地,依然垂着眼眸,这个角度,却能望见,他的锦靴踏过青砖地上的薄雪,一截修长的影子,逐渐罩住她。
锦靴顿在一步之遥的地方,他忽然解下了身上大氅,披在她身上。
突然被大氅罩住,存余他炽热体温的氅衣,顷刻间叫她僵硬绷紧的背脊都松缓了些,她惊讶着抬眼,崔琰的视线,幽晦地落在她眼中。
她猜不透他的想法。
他的想法,好似天上的云般不可捉摸。
但她却看得出,他这时眼底染有薄薄的情霭。
他幽幽俯身,两手捧着她巴掌大的脸颊,声音似乎哑了些,目光晦暗:“朕说的话,你一点也不记得,不放在心上。”
离得这么近,动作更是突然,云蓝全然不知他在说什么,只愣愣的。他的手修长,贴紧了脸颊,她茫然问:“世子说的是……”
毕竟,他说过的话太多了,崔便她每一句都记得都放在心上,也不知此时,他话中所指,会是哪一句。
他的冕旒垂晃着,各色的宝珠折射出一两星微弱光泽,挡在她和他之间。
他眸色更沉,嗓音与这夜朔雪一般寒冷:“朕说过,‘除了你,谁也不行’。”
云蓝心头猛地记起来,不久前,他的确说,他……需要一个长子,除了她,谁也不行。
所以他今夜才……,才明知谢疏云等在涵元殿向他自荐枕席,他却不去?
是因为这个?
——
谢疏云在涵元殿的长廊上已等候了很久,张望着,却怎么也不见崔琰回来。
母亲说要绊住他一会儿,从而给她准备的时间,可现下,时近破晓